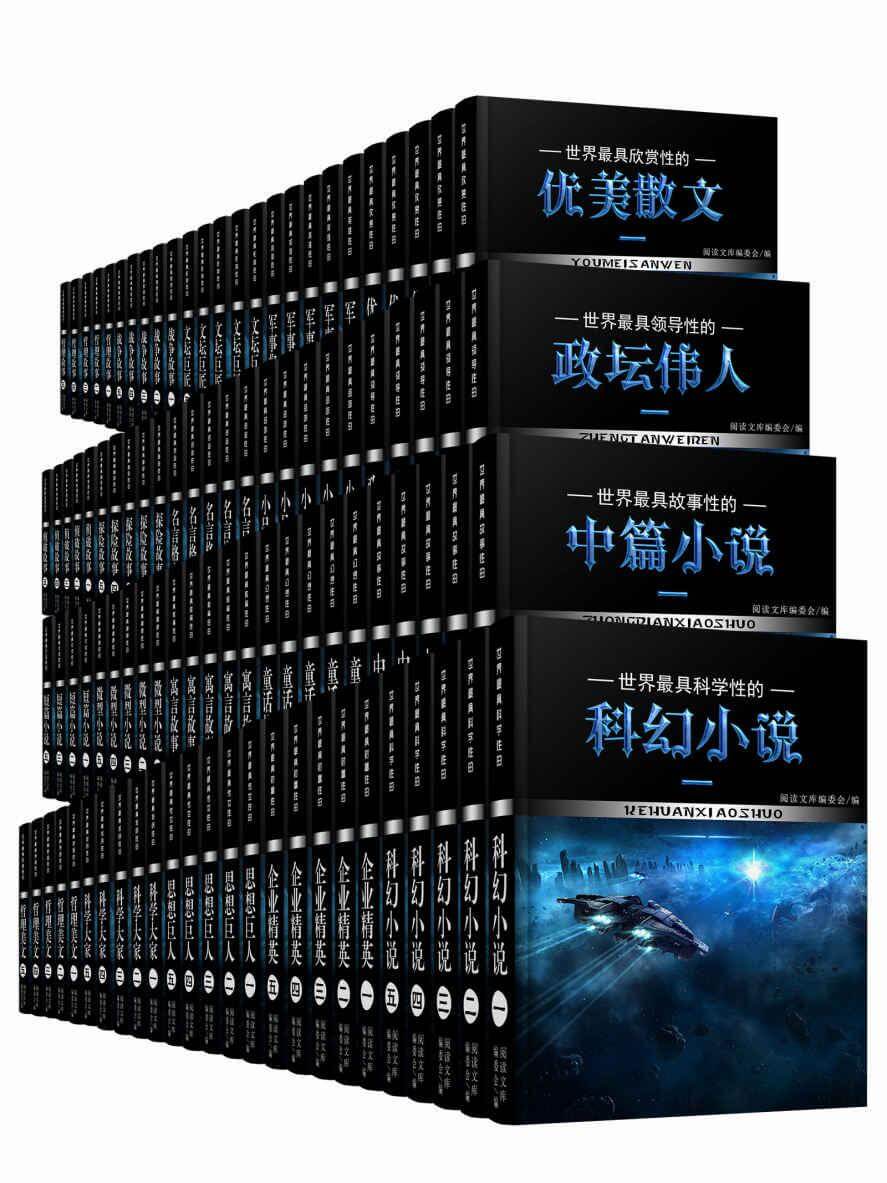简介
希瑟发现自己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抑郁症的深渊,这是她经历过的最黑暗、最漫长的一段时期。为了她自己和她的家人,希瑟决定冒险参加一项临床试验。
在本书中,希瑟讲述了18个月来她所忍受的痛苦和她的自杀倾向,以及长达一个月的实验治疗过程。在治疗过程中,医生通过麻醉让受试者的大脑陷入整整15分钟的脑死亡,然后再把她从沉睡的状态中拉回来。这样的实验进行了十次。虽然过程艰难,但治愈的开关被打开了,希瑟从此再也没有经历过任何自杀式抑郁症。
这位诚实、坦率的痊愈者讲述了发现自己患上抑郁症可能面临的情况,以及家人该如何真正理解抑郁症患者的处境——不一定感同身受,但是能宽容理解。
她是一位单亲妈妈,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全职经营着她的网站,同时还有家族抑郁症遗传史。她勇敢又真诚地向所有抑郁症患者和那些身边有抑郁症患者的读者讲述了自己与抑郁症抗争的过程,以及她是如何战胜抑郁症的。
作者介绍
希瑟·B.阿姆斯特朗,《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dooce®网站创始人。她的网站dooce®曾两次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博客Top25之一,《福布斯》杂志也将其列为女性网站百强。她是一位单亲妈妈,拥有十余年抗抑郁的经历,全职经营自己的网站,同时还有家族抑郁症遗传史。
部分摘录:
初次接受治疗的一个月前,我跟我的心理医生约了个时间面谈。这是他要求的,得先进行面谈,他才同意再给我开药。在一般情况下,当我需要再开点儿安定片、加巴喷丁或者曲唑酮的时候,他的秘书会通知药房。但我已经9个多月没去见医生了。他问我为什么没有按时预约,我跟他说,我很忙。我跟每个人都是这样说的。他们无法理解,一个需要全职工作的单身妈妈,每一天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对不起,我不能跟你一起喝咖啡。我不能跟你一起吃午饭,我不能参加读书会,我不能帮忙筹备二年级的万圣节晚会。”我很忙,让人无法理解、近乎疯狂地忙。
但一句“我很忙”却不能让劳里·布什内尔医生就此罢休。他是大学神经精神研究所(UNI)电休克疗法(ECT)中心的主任,办公地点在犹他大学。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坐在他对面,身体如死尸般僵直。布什内尔医生忽地把笔记本放在桌子上,有点儿生气地斜了斜下巴。他解释道,抑郁一旦发作,越是长时间放任不管,病人就越难从谷底爬出来。他对我很生气,摇了摇头。我怎么就能这么长时间放任不管它?为什么我等了一年多才来找他求助?当抑郁症状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给他打电话?
答案很长,也很复杂,所以我用一句话总结为:“如果我前夫知道我这么抑郁,他会想办法把孩子们夺走的。”
我终于把这话大声说了出来,这次不是对着我母亲或者谈话治疗师。通常,我都是尖叫着跟我母亲说出这句话的。我深刻地记得前夫威胁我的话,他说他要把我的孩子们抢走。每天早晨,每天中午,每天晚上,每个忙碌的时刻,还有“每件必须做的事情”,所有这一切统统被笼罩在这个无比真实的威胁之下。他说,我身上那种“一直存在的自杀意念”已经使我不配再当母亲。但在他还没来得及在权威人士面前力证这一点,好剥夺我的抚养权的时候,他就搬去了纽约。3年多来,我竭尽全力,一面抚养两个女儿长大,一面全职工作。我觉得,凡是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脑海里肯定都一次、两次,或者很多次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要是明天能不醒过来就好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自杀倾向或者不想活了。我们知道没有这个选择,我们是永远不会这样对待孩子们的。我们只是想休息一下,而有时候休息的可能性实在渺茫得令人绝望。
“希瑟,如果你前夫发现了,他会怎样做并不重要,你如果死了,这一切就更不重要了!那时候他肯定会发现的!”布什内尔医生这样说道。我还没跟他说,我非常愿意死。如果从病人口中听到这个字眼或者类似的字眼,医护人员是要履行某些义务的。我不想被强制送进某种机构。但我什么都不必说。
“一般我会问问你的感受,但现在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你脸上已经写满了,你的眼神都被偷走了。”
他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了手机。过了一会儿,他拿着手机回来了。他再一次坐在我对面,对我说:“我有个想法,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他刚才给他同事——布赖恩·米基医生打了个电话,问他是否还需要更多的患者参加电休克疗法的实验研究。我一直在旁边坐着,一动不动。米基医生正在研究另一种电休克疗法,这种电休克导致的抽搐副作用可能相对更少。他听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人用异氟醚麻醉,来模仿电休克疗法。但在米基医生的研究中,他首次使用异丙酚麻醉来模仿电休克,这种药的副作用相对不那么强烈。
布什内尔医生跟我解释说,这种疗法就是通过静脉注射麻醉患者,让患者直接进入睡眠状态,大概每星期3次,一共10个疗程。这项研究是为了弄清楚“暴发抑制”,也就是让脑电波活动平静下来,能否缓解抑郁的症状。说是让脑电波活动“平静”下来,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让脑电波活动“降至零”,或者“近乎脑死亡”。布什内尔医生更喜欢将之称为“一次让人自我感觉更好的诱导性深度昏迷”。麻醉师把这叫作“深渊”。
“她现在就在我办公室里坐着呢,”布什内尔医生跟米基医生这样说道,“嗯,好的。我跟她说。”挂了电话,他跟我一一介绍了这项研究的细节,问我愿不愿意看看正式的文件。
“希瑟,你是最完美的研究对象。”布什内尔医生说,“你有抑郁史,你们家族也有抑郁史。最近一次抑郁发作已经持续了一年以上。你年轻,又健康,而且……”医生停顿了一下,两手放在膝盖上,身子往前倾了倾,“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这肯定能行。”
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沓文件,还有一份我最终会签字的免责声明。这份声明意味着,如果我在这10次濒死的过程中出现了任何意外,医院和所有跟这项研究相关的人员都不用承担责任。治疗的地点跟布什内尔医生的办公室就隔着一条走廊,在大学神经精神研究所南侧的电休克疗法中心,这栋建筑坐落在名叫“虹彩路”(Colorow Way)的蜿蜒小道上。我开车离开停车场,去超市买了两个金色的聚酯薄膜气球——超大的数字“1”和“3”,因为那天是利塔13岁生日。我要给她的几个朋友准备生日派对,而气球最能营造欢乐的气氛。
“没想到一充上氦气,这数字气球会变这么大!”我对一位帮我拿货的女士这样说道。我一边发愁到底该怎么把这么大的玩意儿塞进车里,一边想着布什内尔医生刚刚跟我说的那番话。
“谁都想不到!”那位女士一边给数字“1”扎口,一边这样说。
“等会儿我把两个数字一颠倒,大家就会以为是我过31岁生日,”我这样说道,“我看起来绝对可以再年轻十多岁。”我一边说,一边夸张地用手从头到脚比画了一下,仿佛在展示一位大美女,只不过这位美女穿着破旧的灰色连帽衫、黑色的瑜伽裤,她前天晚上睡觉穿的就是这身行头,头发已经6天没洗了。
“亲爱的,”她边给数字“3”充气边接话儿说,“我都快60了,所以我只求自己能跟你一样有气色。”
那位女士在两个气球上各绑了一段缎带。我付了钱,尽量优雅地拿着这两个硕大无比的数字出了门。我的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整个后座都塞满了,我不得不调整后视镜,把脑袋伸出窗外,总算勉强腾挪出了停车场。我女儿今天正式成为一名青少年了,我心里想着,就算我真的撞到了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他们也得原谅我。从商业街开出来的时候,我长舒一口气,觉得自己在笑。
20分钟后,我到了家,我给母亲发信息,问她能不能和我聊一聊。我跟母亲都是这样沟通的,如今这也是大家唯一认可的电话沟通方式。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一部座机,缠绕的电话线就从门底下穿进姐姐的房间,我要打电话的时候就用拳头砸姐姐的房间门。谢天谢地,终于不用生活在那样的地狱里了。母亲立马回了信息:“可以。”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真不知道母亲有多少次都是这么回的。
“我刚才在店里跟一个店员开玩笑了,”电话接通了,母亲刚说了句你好,我就这样脱口而出,“我不知不觉地就这么做了,感觉很正常,很轻松。我都记不起上一次跟别人开玩笑是什么时候了。我不仅跟一个陌生人交流了,还对她笑了。我想不起上次想这么做是什么时候了。”
只要我不是躲在衣橱里朝母亲吼自己想死,只要是跟母亲平心静气地正常打电话,我就会在客厅里绕大圈子。当我第三次路过钢琴的时候,我开始哭起来。母亲问我有没有事。我没事,我真的没事。不光没事,还挺好的。我只是有些不知所措。我眼里满含泪水,只是因为感到紧张。因为只有我是家里最疯的那个,只有我需要去医院接受治疗。还不是去普通医院,而是去那种诊所接受治疗。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地方,那个给精神错乱的人进行电击治疗的地方。
我当然是家里最疯的那个,那个败类,那个脱离摩门教信仰、加入民主党的人。我就是那个蠢蛋。
可尽管如此,这是一年多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希望。我感觉,或许我可以不用一辈子都是这种感觉了。如果什么都不做,我可以肯定,自己的余生将在想死的感觉中度过。我都已经放弃了,想着就这样一辈子想死吧。可是,如果可以改变呢?如果布什内尔医生说的是真的呢?如果治疗有用呢?
“我们做!”母亲打断了我的思绪,向我保证会跟我共渡难关。她的话语坚定有力,不容置疑。
“但你得开车——”
“我才不管我得干什么呢。哪怕叫我飞上月球再飞回来,我也愿意。我们做这个治疗。”
我把精神科医生解释给我的话原样讲给了母亲听。虽然她说她不需要听这些细节,我还是让她听我讲完,好像只有这样我才能对自己感觉到的希望多一份信心。
首先,我得满足一系列相当严苛的条件才能接受治疗。我不能对什么有瘾,不能有人格障碍,不能处于狂躁期。抑郁症发作得超过一年,要达到我现在这种严重程度,而且还得是治疗无效的难治性抑郁。我的情况完全符合,因为我服用抗抑郁药有12年了,已经不管用了,一年前我做出一些调整,但也没怎么起效。虽然我晚上还能入睡,但我吃的药已经无法帮助我正常生活了。其次,电休克疗法是已知的对抗难治性抑郁最有效的方法,哪怕像氯胺酮这样的药物,其有效性也很有限。电休克疗法的原理是通过电击大脑,产生类似于癫痫发作的效果,这会导致大脑活动暂时中止。据说,这正是治疗的关键。就像计算机重启一样。大家都知道,计算机有了问题,有时候只要关机重启几次,就能解决应用程序崩溃的毛病。所以,大多数接受电休克疗法的患者都要经历10~12次的治疗。大脑每重置一次,就会有一点儿好转。再次,以往的研究使用的是叫作异氟醚的麻醉药,效果虽然不错,但麻醉效果比较难退去,会令许多患者烦躁不安,而且总是有恶心的副作用。米基医生针对异氟醚麻醉法,做了更严格的随机研究,但是没有成功。他只好另想他法。异丙酚和异氟醚都能抑制脑电波活动,他产生了用异丙酚做研究的想法,并最终成功了。虽然同为麻醉药,但异丙酚在临床试验中的表现比异氟醚的副作用小多了。正是这些原因,我才同意做这项“在母亲面前死10次”的治疗。
几个月后我才知道,母亲挂上电话的那一刻,便瘫倒在继父怀里哭了。她哭,是因为她从我的声音里听到了希望。在她听来,这简直就是她每夜祈祷召唤的天使的声音。她依然每晚祈祷,召唤天使。整整4个星期之后,治疗开始了。
***
“还有这个……你看到这个瓶子了吗?”那是我第一次接受治疗,麻醉师在跟我一一解释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共有5个麻醉师参与,今天值班的是塔德勒医生。我很感激他这么仔细。我点点头,因为我紧张极了,已经不会说话了。在后面的治疗中,塔德勒医生扶着我的胳膊。我太需要这一丝温暖了,这让我安心。我真的害怕极了。我签了知情同意书,上面列着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有一条是死亡:
风险:
罕见(少于1/10 000):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心跳不规律)、呼吸骤停(无法呼吸)、心肌梗死(心脏病发作)、中风等并发症,甚至死亡。
即便我想死,第二天晚上也得送孩子上钢琴课。我如果死了,她们就迟到了。
“这个是芬太尼,这是一种阿片制剂。给你开这个药,是防止你从麻醉中醒来时头疼。就是这个。”然后,他举起一个稍微大一点儿的瓶子,里面装着乳白色的东西。一名护士和米基医生的研究助理合力用一个正方形的电极片把一条线固定到我的额头上。电极片上的小钩子紧紧地钩在我的皮肤上,我感到一丝疼痛。每次治疗结束后,我在神志不清的时候常常会想,我的额头不是用其他的电极片材质做成的,电极片怎么就贴在我额头上了呢?
护士又检查了一遍,确保连接每种药的管子都牢牢地固定在22号注射针头上。30分钟前,他们把这个针头插进我的血管里,并紧紧地固定在我的胳膊上。天哪,那个针头,那个扎针的整个过程真是太可怕了!我从不怕看见血,也不怕抽血,以前每次都会向抽血医生炫耀一番:“不用看我,你扎就是了。真的,我连眼都不带眨的。”可是,那时我还没见过这样的针头。我第一次看见这个针头的时候,想起了《大白鲨》中罗伊·施奈德饰演的警察第一次瞥见大鲨鱼的情形。
“你需要个大点儿的船。”
我伸出右臂,放在窄窄的桌子上。桌子那头坐着莫莉,她是我第一次治疗时的抽血医生,她正往计算机里输入我的药物史。她一边准备扎针需要用的东西,一边跟我闲聊了几句。要准备的东西可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