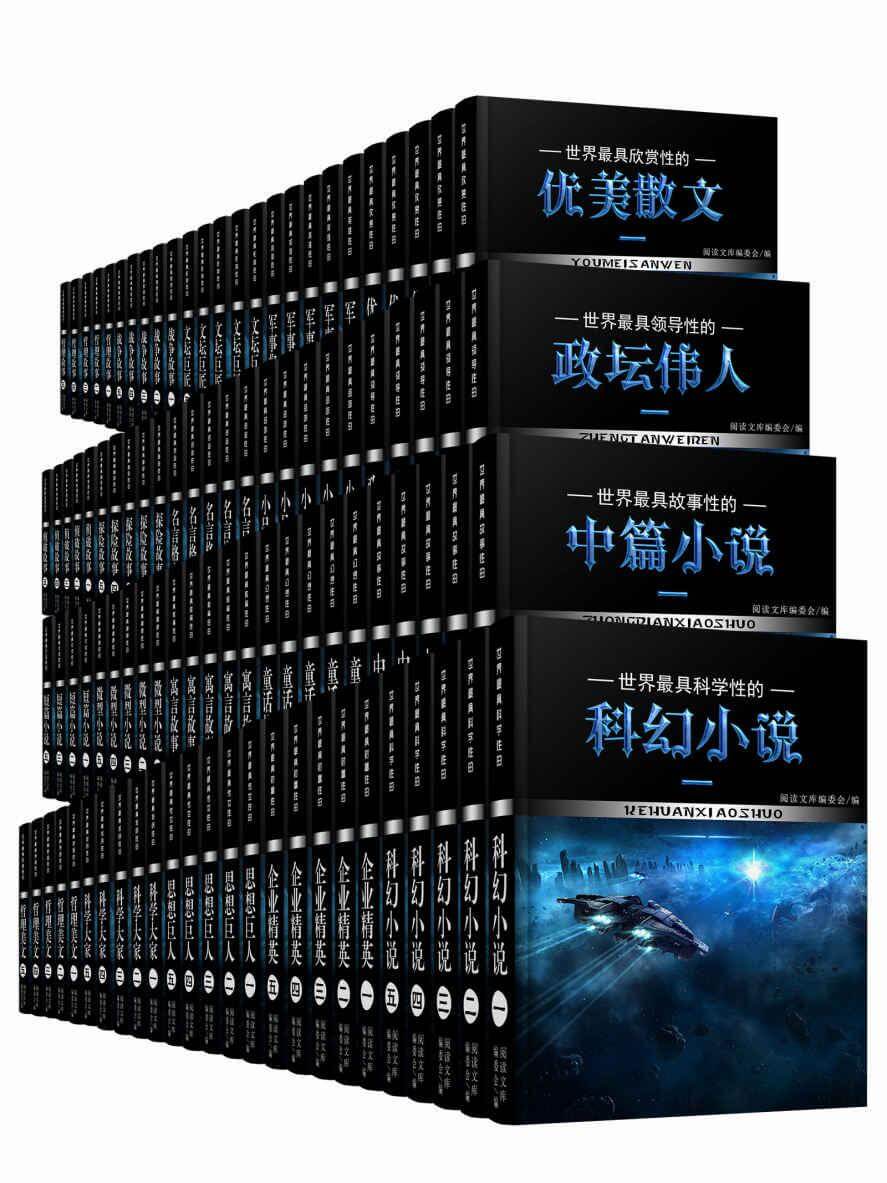简介
大部分人都认为,这只是懒的表现。其实拖延是一种心理,它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问题,它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长久,你了解的著名作家、科学家甚至几十几百年前的名人都拖延。 本书意在阐述拖延症一现象正当和合理性,意在反驳大众对拖延症患者的偏见和谴责,并指出大部分人都会拖延。他引经据典地写出”拖延”一词的起源,又博古通今地介绍了很多文史哲名人和科学家在经历拖延症时作出的反应,很多时候是拖延症帮助他们完成世人所知道的杰作。本书所用的例子大都集中在近现代的欧美,适合被拖延症困扰、想要快速了解欧美名人轶事的读者,也适合对社会学、大众心理学和泛科学感兴趣的读者。
部分摘录:
心理学的“抗拖”之战 今日便让自己明智些吧,拖延乃疯狂之举。
到了明日,这致命的恶习还将延续;
明日复明日,拖尽了此生:
是延宕偷走了良辰。
——爱德华·杨格,《夜思录》
1933年夏,一个名为阿尔伯特·艾利斯的19岁孤独少年,不断尝试同纽约植物园中的女性搭话,约莫从这时起,心理学领域对拖延症的战争打响了。
如今,人们将艾利斯称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但在1933年,他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特别害怕与女性交谈。那时,艾利斯与父母同住在布朗克斯区,离植物园不远。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坐在植物园的长椅上,幻想着自己能鼓起勇气接近在玫瑰丛中闲逛的女性,不论是谁都行。艾利斯特别希望自己能和她们相遇,与她们约会,甚至与其中一位结婚。
后来,艾利斯回忆道:“当时无论我多么费尽心思说服自己,搭讪的时机已经成熟,没过多久我都会临阵脱逃,然后咒骂自己是个孬种。”
艾利斯为此感到心烦意乱,于是为自己安排了一项“家庭作业”。七月间,只要不下雨,艾利斯每天都去植物园,只要看到有姑娘坐在长椅上,就坐到对方身边,准备一分钟左右,然后开始和对方交谈。艾利斯没给自己留一点儿余地——不准找借口、不准打退堂鼓、不准忸怩作态。
他写道:“我没给自己留下拖延、思考的时间,否则只会徒增烦恼。”
艾利斯成功了。那年夏天,他在植物园尝试搭讪了130名女性。其中,30名女性扭头就走,另外的100名女性则愿意和他聊天。出乎他意料的是,有一位女性真的答应和他约会——尽管最后爽约了。不论如何,艾利斯认为自己的试验成功了。他意识到,只要直面让自己手足无措的事(例如和女性说话),就能克服自己的焦虑。这次经历改变了艾利斯的一生。后来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心理学历史也从此改变。”
1913年,艾利斯出生于匹兹堡。父亲常年奔波在外,和他很疏远,而据他描述母亲是个“聒噪的话匣子,从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艾利斯回忆,为了填补父母家庭责任上的空缺,他担负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艾利斯给自己买了个闹钟,这样他就能准时早起给弟弟妹妹穿衣服。艾利斯把自己想象成英雄人物。
1934年,艾利斯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获商学学士学位。几次尝试出版小说均以失败告终后,1947年他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按当时的标准来看,艾利斯刚开始运用的心理治疗方法是极其保守的。他采用的是经典的精神分析法——让患者躺在诊疗台上做梦、幻想、自由联想,然后给他描述梦境,他借此努力找到患者患病的潜意识根源。但是,艾利斯自己由于无法诊断出患者的病因而变得越来越沮丧,他似乎天生就不擅长这种漫长而艰难的治疗方法。于是,他开始宣扬一种更具动态的疗法,“积极主动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坐等奇迹发生”——这句话见于他为威廉·克瑙斯所著的《终结拖延症》一书撰写的前言中。艾利斯以自己克服害怕同女性谈话的办法为基础,建立起一套治疗方法来纠正会弄巧成拙的错误观念,他称之为理性行为疗法(REBT)。
20世纪50年代末,艾利斯开始向别的心理医生传授他的新疗法。他抓住了一个好时机,因为很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一家独大的状况就要被颠覆了。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广受质疑。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彼得·梅达瓦称精神分析学为“20世纪最自以为是的大骗局”,这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艾利斯则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弗洛伊德满嘴喷粪。”艾利斯从不会花上数年时间让患者躺在沙发上与他交谈。他开的处方就是“忘了不堪的过去”,并且行动起来。他说,所谓神经官能症,不过是把“‘哭闹’说得更文绉绉一点”罢了。那些想要深挖自己童年创伤的人都是“巨婴”。
随着艾利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追随者们开始狂热地效仿他的自助法。其中,有些人为了达成心理上的完整(也可能是为了约会),重演了当年艾利斯在植物园的场景,不管不顾地跳到毫无防备的女性面前搭讪。除了教人调情,艾利斯最大的贡献应该是给心理学的实践注入了紧迫感和行动力。19岁时,艾利斯要求自己,“别多想,否则只会徒增烦恼”,从而克服了怕羞的毛病。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艾利斯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意志坚定、精力充沛的形象,在他看来,耍嘴皮子不如立即行动,思前想后不如努力尝试。
认知行为疗法(CBT)是当代主流的心理疗法。而艾利斯的理性行为疗法(REBT)便是认知行为疗法的源头之一。在近几十年中,如果你因为失眠、抑郁、焦虑、药物滥用、社交障碍等问题寻求帮助,那你很可能会通过CBT有所好转。CBT用于发现有害的行为倾向和自我摧残的想法,并根除这种毫无益处的思维。这样看来,艾利斯及其他(如阿朗·贝克)认知行为疗法的先驱者会广受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提出的新疗法与价格不菲、方法复杂、回访无数次的传统心理疗法相比,不仅操作方便,而且价格低廉、浅显易懂。传统疗法要求病人花数年时间谈论自己的童年、做过的梦和隐藏的欲望,而新疗法只需病人完成一系列治疗手册上的任务,同治疗师进行几次精心设计的谈话,就能得出结果。
运用认知行为疗法的心理医生喜欢将这种疗法描述为“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确,CBT治疗手册上的清单、目录、自我检测、问卷调查都简单利落,有一种高效的感觉。这是一种几乎肯定会受到工商管理学硕士欢迎的疗法,因为它确实高效。
*****
但凡有人找寻与拖延症有关的文学作品,就会发现保罗·瑞根贝茨的《代代拖延:拖延症权威史》这本书的观点被引用了很多次。然而,当你想找这本书的时候,会发现很困难,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出版圈内的一个玩笑,是一个恶作剧:因为没有哪个有拖延症的作家能动笔写成一部有关拖延症的权威历史。
尽管如此,威廉·克瑙斯在《终结拖延症》一书中依然对这本并不存在的书籍提出了批评,好像他经过了深入的思考。他写道:“该书的调查很有意思,但没把重点放在解决问题上。”抛开参考文献引用错误不谈,克瑙斯有一点说得没错,即在《终结拖延症》出版之前,缺少讨论如何“解决问题”的书。《终结拖延症》首先向拖延宣战,并提出战胜拖延的策略,之后又诞生了许多与之类似的书籍。尽管《终结拖延症》影响深远,但从现在来看,这本书有不少问题。书中充斥着大量20世纪70年代流行但现在看来不合时宜的陈词滥调。比如,我并不确定书中提到的“自我贬低”是什么意思,但这个词确实开辟了一个时代。克瑙斯还有一种稀奇古怪、令人沮丧的习惯,就是通过拉长单词来表示强调:“你最好在生活中找点麻——烦!”“想要得到转变,必须付出巨大努力,培养一种长期乐观的心态。没错,努——力!”
在《终结拖延症》一书中,克瑙斯布置了一些家庭作业,这些作业和艾利斯当年为了战胜与女性交谈的恐惧时给自己布置的作业异曲同工:一旦拖延,就惩罚自己做不想做的事(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每拖延一次,就给三K党[1]捐50美元);或建立一个针对及时完成该做之事的奖励制度,让自己能够“自然而然地”去做之前一再拖延的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类策略在研究拖延症的经济学、心理学文献中频繁出现。
《终结拖延症》和随后出版的同类书籍像完成组织工作一样,都是用系统的方法来处理拖延症。这种有条不紊的方法自有它的迷人之处,甚至让人无从抗拒。谁没梦想过能实现自我价值呢?谁没发过誓要认真起来、全力以赴,定下运动目标,坚持做仰卧起坐呢?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把不断尝试自我提升,又一一放弃的经验汇集成册,都能装满一座小型图书馆。驱策和拖延都是我们天性使然,这二者就像是双胞胎。可是一直以来,我对这些系统方法心怀疑虑,即认知行为疗法治疗手册上的练习、自我检测、个性化目录、目标陈述等系统方法。从治疗手册说起,有哪个成年人会愿意去做练习题啊?这就像让他们去完成小学一年级的拼写题一样,是对他们的侮辱。练习题这种东西是给未成年的小孩子用的——他们用铅笔在试卷最上端用笨拙的字体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坐在整体式书桌旁,弯着身子做练习,书桌盖能抬起来,不让老师看见他们在做什么。但是人过了一定年纪(应该是18岁吧?)就无须再做基础的练习题了。
说得更确切些,多数有关自我提升的方法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它们对于太多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的事物——比如一件件扑朔迷离的琐事、一次次冥思苦想、一个个未被满足的渴望——都毫无办法。对艾利斯而言,拖延背离人们所期望的行为规范,是失败的表现。再加上艾利斯把自己视作英雄,根本无法忍受拖延,并把拖延等同于“极度怯懦”。艾利斯参与编写的《认知行为治疗手册》对想要拖延的念头与倾向拖延的思维方式提出质疑,从而抨击拖延行为。当惊慌失措的飞机乘客、战战兢兢的演讲者、执拗的拖延者受到质问:“你有哪些证据来支持你的思维方式?难道没有其他更健康的思维方式吗?”虽然这些都是常识,但是任何一个拖延症患者,任何一个惊慌的飞机乘客都会给出这样的回答: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即便是常识也无法轻易撼动。
*****
我能想到试图向乔·法拉利讲述我对拖延症的热爱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仿佛预约了家庭医生,跟他商量你打算每天多抽两包烟一样。
法拉利是德保罗大学的教授,在拖延症研究领域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之多,这世上大概无人能比肩。查阅与之相关的文献,你就会发现乔·法拉利这个名字出现得有多么频繁。
当我决定写一本与拖延症有关的书时,法拉利就是我第一个联系的人。我看过他写的一本关于拖延症患者战胜拖延习惯的行动指南,所以我觉得法拉利会告诉我他治疗拖延症的方法有多么管用。他答应来纽约的时候和我见一面。我和他约好,到时候我会开着我那辆老旧的丰田卡罗拉去机场接他,然后送他去他想去的地方。我们在机场碰面时,法拉利的一只胳膊下夹着马克斯·昂加马尔的《论守时、准时、近代加尔文主义早期的自律》,他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收下礼物后,我暗忖,法拉利是否发觉我晚到了一小会儿。
我们计划开车去伍德赛德的一家餐厅,离这里不远,干净卫生,夹在两座公墓和布鲁克林至皇后区的高速公路之间。他虽然不是本地人,却似乎比我更了解开车的最佳路线。所以,一路上,哪个路口该转弯,什么时候该变换车道,还要往前开多远,我都听他的。车子穿梭在皇后区的这段时间,他开始和我分享他了解的关于拖延症的知识。
指路间隙,法拉利说:“我把拖延症患者称为‘老磨’。他们通常都很聪明。他们必须得聪明,这样才能不停地编出说服自己的借口。”
法拉利一直以来都在撰写、讨论、教授有关拖延症的内容,他研究拖延症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理所当然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我很欣赏法拉利,钦佩他对拖延症的研究热情,但在我们初次见面期间,有时我觉得他会将别人拖延的行为,尤其是我的拖延行为当成是对他个人的侮辱。
法拉利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拖延症产生兴趣的,当时他在纽约阿德菲大学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在一次关于自我挫败行为的课堂讨论上,他向一位教授请教,询问之前是否有学者把拖延症作为一种自我设限策略来进行研究。教授让法拉利自己去图书馆找答案。结果,法拉利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
法拉利说:“这方面的研究一个都没有,充其量只查找到认为拖延症是写作的障碍之类的文章。”发现拖延症和自我设限行为这个领域有很大研究空间之后,法拉利就将其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他解释道,自我设限即自我挫败的一种方式,原因可能在于害怕搞砸某事或害怕做成某事。有自我设限倾向的拖延症患者会拖延自认为力所不能及的工作。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除了这份工作让他们手足无措,还有一点,即拖延行为能在失败面前为他们撑起保护伞。一旦失败,他们就会说那是因为自己没有全力以赴、因为自己在最后一刻才动手、因为秉持了“去他的吧”的态度。拖延行为让拖延症患者在面对失败时找到了借口,如果未能完成任务,拖延行为难辞其咎。
“这是人们避免焦虑的一种方法。”法拉利对我说,“习惯性拖延症患者宁愿别人觉得他不上进,也不愿别人觉得他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