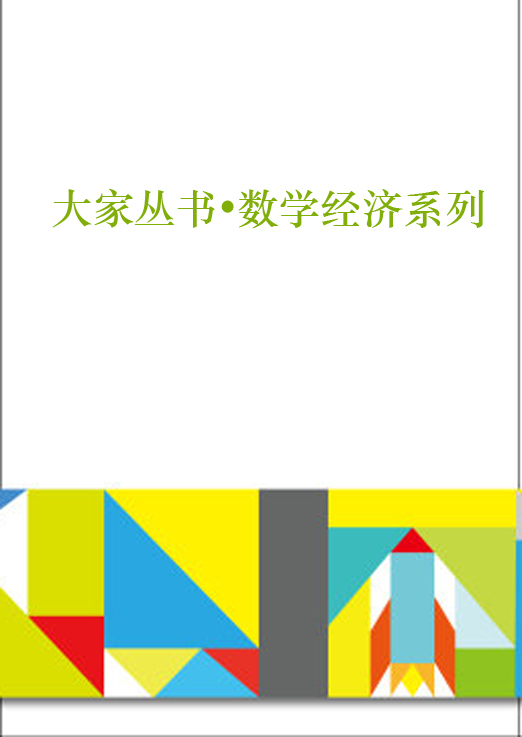简介
这是一部从战略、技术、人才和管理4个维度全面阐述企业数字化转型方法论的著作,是国《明哲文选》收录了全球著名战略学者陈明哲教授过去30年来的代表性著作,内容涉及学术、企业实务以及教育等多个方面,展现了陈明哲教授在中西文化冲击与交融以及学术与实务脱节和分裂的背景下,所开辟的独特的学术创业之路。这套文选旨在帮助读者深入了解陈明哲教授“精一”和“双融”的思想理念,以及华夏智慧的行践心得,也期许读者回归自己,反思如何在动荡的大环境下,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处。
《明哲文选》系列之一《承传行践:全方位管理学者的淬炼》是整部文选的总纲,融合了严谨学术论文、演绎应用文章、媒体采访报道、学者及企业家点评等多种体裁形式;全书从陈明哲教授忆父怀师的真情抒怀,以至他服务社群的心得反思,如实呈现陈明哲教授成为一位全方位管理学者的心路历程。
作者介绍
陈明哲
现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讲席教授、国际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暨战略管理学会(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终身院士,是全球著名的企业战略专家,也是动态竞争理论与文化双融理论的创始人。
陈明哲教授曾担任全球拥有2万名会员的国际管理学会的主席(2012 ~ 2013年),并于2014年获得该学会的“杰出教育家”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对管理教育与实务的卓越贡献。陈明哲教授是一位平衡专业与人文、理论与实务的全方位学者,不仅是学术创业者,更是致力于“立人立群”与“薪火相传”的导师,迄今已在全球各地培养了逾万名管理学术与实务人才。
部分摘录:
1989年秋天,陈明哲在新泽西海边参加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主办的学术精英工作坊,当时他刚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陈明哲在工作坊的一项任务是宣读评论“战略群组”(strategic group)的论文。当时,“战略群组”是一个热门的学术议题,光是那一年,探讨这个话题的博士论文就有33篇。而陈明哲在评论中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战略群组方法对竞争者分析并不是那么有用。
当时在座的有许多学术界的大人物,而陈明哲只是个学术新人。他的发言遭到了非常严苛甚至刻薄的反弹。为了平复自己的心情,他开了两个小时车去另外一个小镇。在那里,他买了一幅油画,画中是一艘船在狂风怒浪里航行。
出国后,全新的生活环境中处处都是挑战:论文多次被退稿,如何调整自己?日复一日地辛勤研究,是否真的能有成果?如何把握分寸,处理学术界的人际关系?如何在人才济济、竞争激烈的顶尖名校里生存下来,脱颖而出……“学术界和其他行业一样,有最好的一面,也有最坏的一面。日后,当我面对横逆,姜老师在我临行前送给我的两个词——决心(determination)与坚持(persistence),始终是驱策我往前迈进、追求精一的动力。”
陈明哲时常会提起姜占魁的一段往事:当年,姜老师在台湾大学英文系读书,一本本“啃”英文书,一本本“背”英文书。一个大男人,读书读到瘦得只有37公斤!
“一个大男人,读书读到瘦得只有37公斤。”如果放在今天的语境中,这恐怕会令人颇为费解,甚至招致讪笑——这不就是个书呆子?!然而,当我们了解了姜老师经历过什么,才能多少明白这句话背后的意味。
“先生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县,家境清贫,成长期间历经战乱,颠沛流离。14岁离家赴县城求学,为全村仅有的两个中学生之一。”(台大校史馆)
姜占魁,曾是中国千百万流亡学生之一。
“现代中国,有个名词叫流亡学生,它前后有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第二梯次,‘七七抗战’开始,沿海各省青年内迁。第三梯次,内战期间,各地青年外逃……流亡的青年千万百万,流亡很苦,很孤独,有时也壮烈,危险。”姜占魁的同代人,且是山东老乡的台湾作家王鼎钧在回忆录《怒目少年》中写道。
1942年,王鼎钧17岁,离开家乡山东兰陵,前往安徽阜阳。同一年,14岁的姜占魁也开始了流亡生涯,先赴县城求学,后随校辗转至青岛。
“那时,山东省是沦陷区,日本控制学校,修改文史课程,培养以日本为宗主的思想,办理各种亲日活动……高压之下,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可以苟全。年轻人血气方刚,心里窝着一把火,留在家里很危险……家长们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出去。”(引自《怒目少年》)而当时,国共两党都成立了战时学校,收容流亡学生,在硝烟炮火中一路求生、一路读书。
“先生(姜占魁)14岁离家,在四年物资匮乏的学校生活中,曾因饥饿缺粮濒临死亡……1948年,先生离开青岛转赴南京,幸得同乡协助,在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旁听。正当此时,先生罹患重病昏迷,醒来时,身上所有皆被偷光,只得将仅存之大衣向农家老妇换来一袋鸡蛋和少许米麸,得以撑到广州,不致沦为饿殍。”(台大校史馆)
流亡学生中,有的半途投笔从戎,有的自谋生路,有的则将读书向学作为风雨飘摇中的精神支柱、生存支柱。
“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游兵散勇及不愿做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道路上塞了各种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生,一片泥泞。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地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齐邦媛,《巨流河》)
“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和自信。”(齐邦媛,《巨流河》)
“流亡学校”的创办者有政府、军人、教育家,形形色色,因为他们的心力、能力、物力之不同,其所创办的“流亡学校”也千差万别。然“为国家民族保存一点读书的种子”,却是彼时中国共同的愿力。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留踞海南岛做最后挣扎。21岁的姜占魁亦流亡至海南岛海口师范学院。后解放军挥师南下,姜占魁便追随恩师邓文礼先生(后任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渡海来台。
“到了台湾,先生举目无亲,生活困顿,依然奋发图强重拾书本。1950年如愿考上台湾大学外文系,却于体检时发现罹患二期肺病,必须强制休学。校长傅斯年先生得知,特别拨款补充伙食。先生经过调养,身体得以康复并复学。在台湾大学四年期间,先生披星戴月寒窗苦读,从来不敢有须臾享乐或松懈,终以优异成绩毕业。”(台大校史馆)
2.4 尽己之谓忠 “公共行政和组织管理,是姜老师一辈子的研究课题。其中,他又专注于组织架构的优化健全,台湾当局如何改变叠床架屋、权责不清的问题,如何通过建立更好的制度引进和任用人才。姜老师就是踏实、勤勉地翻译、出书,然后结合台湾的实际情况,传播给台湾当局和企业界。当时台湾有一批这样的学人,比如杨必立、许士军、吴静吉、林英峰、黄国隆、刘水深、司徒达贤……这些前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心付出,在台湾共同建立了管理学学科体系。”(陈明哲)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管理学在台湾应运勃兴。
新兴的管理学积极地和政府、企业、社会互动。“我觉得姜老师那代人做得很好,从无到有,实实在在、很扎实。他们不仅贡献了思想资源,更贡献了求真务实的风气。”陈明哲说。
“姜老师是政大送出去培养的,苦读12年,回来后是台湾学界为数不多的美国博士。按理说,以姜老师的学养应该留在政大,但他受到了排挤。最初去中兴教书,也是无奈,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学者如何在逆境中看大、看远,如何‘尽己’。”(陈明哲)
“1974年,中兴大学法商学院成立公共政策研究所,在校长罗云平先生力邀下,(姜占魁)接掌第二任所长,对所务发展和教学鞠躬尽瘁,直至退休。”(台大校史馆)
“坦白讲,中兴大学在当时不是很好的学校。当年,台湾最好的公共行政学是政大的,而姜老师到了中兴后,中兴的公共行政学很好地发展了起来,跃升到(全台湾)第二第三。”(陈明哲)
姜占魁一口山东腔,神情节制、淡然,看起来是个很“中国”的读书人,可陈明哲记得,姜占魁却有个“洋派”的习惯——只要去上课,他总是穿西装、打领带。这份“洋派”在当时台湾的大学里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