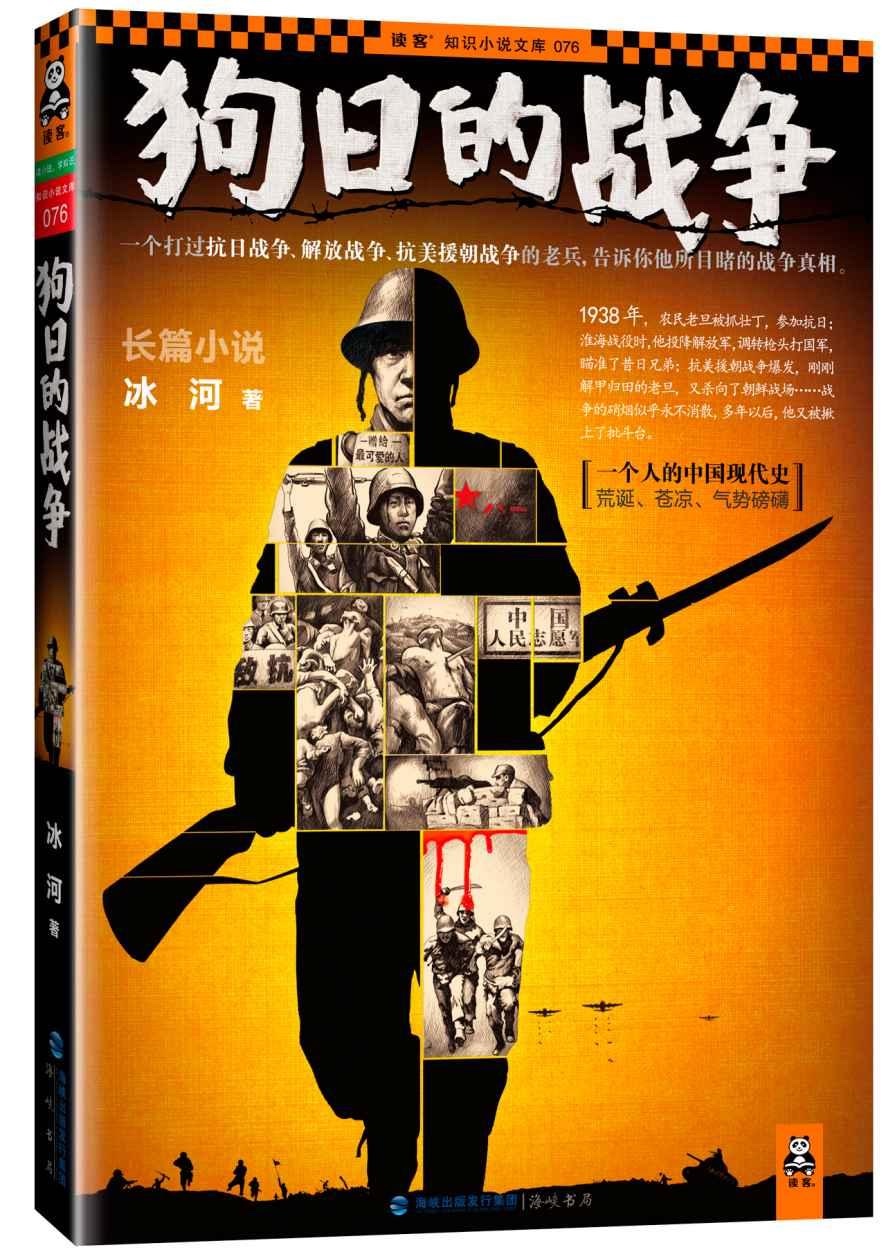简介
·一个惊心动魄的探险故事
再现达伽马的成就和荣耀
·2012年《纽约时报书评》年度优秀图书
·这是一部有关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航海探险的著作。历史学家奈杰尔•克利夫利用新发现的材料,即达伽马水手的日记,以及难得一见的达伽马与印度土邦(现在的喀拉拉邦)首领之间的通信,对达伽马的开拓性航行做了全面、根本性地重新诠释,揭示了这些航行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斗争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这些航行中的一系列事件永久性地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关系。
·本书作者在书的开篇即写道,达伽马和哥伦布这两位探险家 “目标一致,都是寻找通往亚洲的航线,但长期以来,哥伦布那个伟大的错误却一直令瓦斯科•达伽马的成就黯然失色。既然我们要回到他们那个时代——回到那个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东方的世界——现在应当总算可以恢复对二人地位的公正评价”。
作者介绍
奈杰尔•克利夫,历史学家、传记作者,牛津大学哈里斯•曼彻斯特学院 (Harris Manchester College) 研究员。他曾担任伦敦《泰晤士报》的戏剧和电影评论家,也是《经济学人》等出版物的供稿人。他的第一部著作《莎士比亚骚乱:19世纪美国的复仇、戏剧和死亡》(The Shakespeare Riots: Revenge, Drama, and Death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是“国家艺术创作奖”(National Award for Arts Writing)最终入围作品,并入选2007年《华盛顿邮报》最佳非虚构类作品。本书是其第二部作品,荣获2012年《纽约时报书评》年度优秀图书。他最近新译了《马可•波罗游记》。克利夫现住在伦敦。
部分摘录:
1.东方与西方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第一次听到真主这个词,是在610年前后,那时他还无意建立一个世界帝国。
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神志清醒。
“抱紧我!”这位40岁的商人说,他可怜地打着寒战,爬向自己的妻子,妻子拿了个斗篷披在他身上,抱住了哭泣的他,抚摸着他的头发。他一直在麦加城外一处常去的洞穴里冥想——这是娶了大他15岁的寡妇带来的奢侈——天使吉卜利勒[1]就是在那时出现的,让他陷入了痛苦而狂喜的失神状态,还对他传达了真主的告谕。穆罕默德惊恐不已,他以为自己疯了,打算自行跳下山崖。但那个声音不断在他耳边萦绕,三年后,穆罕默德开始公开传道。神谕日渐清晰:对亚伯拉罕和耶稣的信仰确是真知,但它已经堕落了。世上只有一个真主,祂需要伊斯兰——完全顺从。
对麦加的统治者们来说,这真是个坏消息,朝圣者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座城市参拜360处神殿,这让前者获取了丰厚的利润。麦加是在汉志[2]地区一个繁荣的绿洲上发展起来的,那里燥热的山峦屏障沿着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海滨一直伸展出去。它的威严从坐落在城市中心的圣殿克尔白天房[3],那个供奉着阿拉伯人主要偶像的“方屋”,向四周辐射开去。朝圣者每年从沙漠蜂拥而至,膜拜这个神圣的所在:绕着那个石立方转七圈,伸长脖子去亲吻方屋的每一个角落,直到被拥挤的人群推回人流的旋涡。长期以来,古莱什[4]部落精心策划,把他们对克尔白天房的守护演变成对麦加商业命脉的钳制,穆罕默德最初揭露的腐化堕落就是直接针对他们的。他指责这些贪婪的古莱什人中断了阿拉伯社会的平等进程:他们剥削弱者,奴役贫民,无视理应照顾受欺压的贫苦人的责任。真主注意到了这一切,他们全都会下火狱。
激怒古莱什人的倒不是穆罕默德关于唯一的仁慈真主的说法,甚至不是他宣称自己是真主的代言人这一说法。北方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王国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克尔白天房里,耶稣和玛丽的塑像也骄傲地伫立在众多偶像之间。在阿拉伯半岛,犹太移民的影响力还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阿拉伯人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同胞,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长子伊斯玛仪[5]的后代,很多阿拉伯人认为他们的至高神就是犹太人的神[6]。在穆罕默德的时代,诗人-传道者们常年在沙漠上漫游,规劝部落成员放弃偶像崇拜,回归到祖先的纯粹一神论上来。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无可争议的了;让古莱什人感到最不能容忍的是,穆罕默德是自己人。他的家族,哈希姆家族,是古莱什人的一个小分支。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商人,是社会微小而坚实的栋梁,而他却背叛了自己的族人。
古莱什人用尽了一切办法,贿赂、抵制、诋毁这个棘手的传道者,最后还使出了深夜行刺的手段。穆罕默德及时溜出了住处,躲开了刀刃,逃往一个遥远的绿洲定居点——后来的“先知之城”麦地那。随着忠实拥护者的不断增多,他在那里建起了在麦加时梦寐以求的全新社会——乌玛(ummah),意即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让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不是出身,而是忠诚,人们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将赋予女性前所未有的权利,并将财富重新分配给最贫苦的人。穆罕默德获得的启示越来越多,他开始相信,真主选择他的目的不仅是向族人传递警告,还是让他成为真主派遣到人间的“使者”。
为了把圣谕传播出去,他首先要对付麦加。与古莱什人的惨烈战争持续了八年,伊斯兰教的建立过程充满血腥。在最黑暗的时刻,穆罕默德的脸被人砸伤,满是鲜血,他还被手下的一名武士拉出战场,四处散播他已死的谣言——这才算救了他那些残兵剩将的命。乌玛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但就是在那时,穆罕默德向战士们做出了响彻历史的承诺。他得到启示:在战争中被杀戮的人全都会进入最高阶的天堂,“住在园圃之中、泉源之滨,穿着绫罗绸缎,相向而坐。……我将以美目的处女,做他们的伴侣”[7]。[8]
穆斯林——“顺从之人”——继续坚持,而克服困难、战胜命运本身就像是神佑的征兆。决定性的时刻并非战场上的胜利,而是一记公关妙招。628年,穆罕默德出人意料地带着1000名手无寸铁的朝圣者现身麦加,声称作为阿拉伯人,在克尔白天房礼拜是他的合法权利。在他庄严地履行仪式时,古莱什人只能恼火地站在一旁,麦加的统治者们突然显得愚蠢而非不可战胜的,对手的力量就此瓦解。630年,穆罕默德终于带着大批教徒重返麦加。他再一次绕着圣地走了七圈,吟咏着“真主至大!”,然后爬进天房,把偶像都搬了出来,在地上砸个粉碎。
两年后,穆罕默德去世时,他实现了史上无人想象过的壮举:他创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信仰和一个不断扩张的新国家,两者密不可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伊斯兰军队粉碎了那些对新秩序负隅顽抗的阿拉伯部落,这也是阿拉伯半岛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单一统治者和单一信仰的统一。因为宗教狂热、因为有了新的共同目标,还有生则享有大量战利品、死则获得永生的美好承诺,真主的新选民们把目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
他们看到的,是两个超级强权极尽所能要把对方置于死地。
逾千年来,东方和西方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两岸对峙着,这块肥沃的土地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文明的摇篮,如今则是伊拉克的领土。东边是辉煌的波斯帝国,它守护着一个古老优雅的文化和世上第一个天启宗教,即先知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er)所创的一神论信仰,这种信仰因其创建者的拉丁化名字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而得名琐教——它的内容涉及创世、复活、救世、启示、天堂与地狱,以及一位年轻处女诞下的救世主,其出生的年代先于耶稣数个世纪。在历任沙汗沙[9](意为“众王之王”)的领导下,波斯人一直视希腊人为死敌,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彻底击溃了他们的军队。波斯国力复兴之后,便转而与希腊的继承者罗马人为敌。古代的争斗是东西方冲突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而到了610年,也就是穆罕默德最初得到真主的启示之时,这种冲突终于爆发为全面战争。
看到一波波野蛮人在西欧肆虐,君士坦丁大帝在欧洲的东部边缘建造了一个新罗马。光彩夺目的君士坦丁堡遥望着博斯普鲁斯海峡[10]对岸,在亚洲,这一战略意义重大的狭长水域把黑海的水注入地中海。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躲藏在坚固的城墙后面,眼睁睁地看着波斯人洗劫他们富裕的东部省份,直奔神圣的耶路撒冷而去。很久以前,罗马人曾把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夷为平地,并在据称是耶稣受难地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基督教城市;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本人也曾在传说中耶稣受难、下葬和复活的地方建造了圣墓大教堂[11]。如今,让基督徒如末日来临般痛心的是,波斯人拉走了据信耶稣被钉死于其上的“真十字架”,随之消失的还有“圣海绵”[12]和“圣枪”[13],以及这座城市的牧首。在漆黑的天空下,波斯人把圣墓大教堂洗劫一空之后,付之一炬。[14]
就在即将被历史湮没之时,罗马人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波斯则陷入了内战。但胜利者也筋疲力尽。罗马的城市变成废墟,处处是无家可归之人,田园荒芜,贸易中止,人人都受够了为拯救帝国而缴纳的苛捐杂税。在基督教争论不断的时代[15],破坏性最大的是君士坦丁堡在领土范围内强制推行自己的正统基督教的做法。罗马人起初把基督徒投入狮口,现在又转而迫害那些不顺从官方说法的人,在地中海东部的大片土地上,从北方的亚美尼亚到南方的埃及,持不同见解的基督徒望眼欲穿地盼着新政权的诞生。[16]
阿拉伯人以惊人的逞强之势,对两个古老的帝国发起了攻击。
636年,延续了11个世纪的波斯帝国或许就要在一场怒吼的大象冲锋中,在未来的巴格达所在地附近走向毁灭。“该死的世界,该死的时间,该死的命运,”伊朗的民族史诗如此悲叹道,“野蛮的阿拉伯人已经来到,要把我变成穆斯林”。[17]伊斯兰国家的道路北接亚美尼亚,其东北方是与中国接壤的亚洲大草原,东南方是阿富汗,再往前便是印度。同年,一支阿拉伯军队在叶尔穆克战役[18]中击败了人数远胜于它的罗马军队,并占领了叙利亚。正是在叙利亚,大数的扫罗[19]曾在前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皈依了基督教,并在安提阿[20]建立了第一个基督教会组织。第二年,耶路撒冷因饥荒而就范[21],向新的征服者敞开了城门,此时距离罗马人得意扬扬地把“真十字架”物归原位不过区区八年。这座被各种信仰撕裂的城市对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来说都是神圣的所在,罗马人和犹太人为争夺圣地而持续数百年的争斗,就这样为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绵延数个世纪的冲突所取代。
四年后,罗马帝国最富裕的省份——肥沃富有的埃及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就在君士坦丁堡孤立无援之时,被其贬为撒拉逊人[22]——“住帐篷的人”——的野蛮沙漠部落成员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占领了他们近来重新征服的所有土地。众多王国和帝国荣耀尽失,纷纷陷落,就连主教们也开始怀疑穆罕默德是否真的受命于天。[23]
伊斯兰军队从埃及出发,一路向西,穿过非洲的地中海沿岸——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看似势不可当的突进却在那里停了下来。
部分麻烦来自国内。穆罕默德尚未指定继承人便去世了,甚至没有留下关于如何选择继任者的明确指示。世敌恩仇很快重燃,为争夺沙漠中一望无际的商队暗地携来的战利品,竞争更加激烈,而这些战利品无一例外都落入了古莱什人囊中,穆罕默德曾严厉指责的正是这个部落的垄断和贪婪。部落间一番尔虞我诈之后,首批四位哈里发——先知的“继任者”总算从穆罕默德的密友和家族中被选了出来,但即使身居如此高位也未能保护他们不受攻击。一个愤怒的波斯士兵在第二位哈里发做礼拜时从背后捅了他,把匕首插进他的肚子,将他开膛破肚。一群秘密结社的穆斯林士兵不满第三位哈里发的奢华生活和明目张胆的裙带关系,用重棒击杀了他,乌玛因此爆发了内战。第四位哈里发阿里——他是先知的堂弟和女婿,也是先知最亲密的心腹——因为过于积极地与他的穆斯林同胞谈判,在清真寺的台阶上被人用毒剑刺杀了。[24]他的追随者们始终认为阿里是被穆罕默德亲自净身的继任者,并最终集结为“阿里党”——简称为“什叶派”,是彻底从实用主义的多数派中分裂出来的,后者即所谓的“逊尼派”,“逊尼”的词源意为“先知指明的道路”。
第一个哈里发王朝,即倭马亚王朝[25],在动荡中成立了,它把首都迁出混乱恐怖的阿拉伯,以古老的国际都市大马士革为基地,实施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统治。然而敌对势力仍频频进犯年轻的帝国,这一次麻烦来自外部。阿拉伯军队在北非被衣衫褴褛的蓝眼睛柏柏尔人[26]游牧部落阻隔了数十年,后者是该地区历史悠久的原著居民。此前,一波又一波的征服者造访时,柏柏尔人每次都会从山中的堡垒直冲而下,而且他们一般不会仅仅因为宣称皈依了新信仰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冲锋打头阵的是被阿拉伯人称为卡希娜或“女先知”的一个可怕的犹太勇士女王,她披着赤红的卷发驰骋战场,把入侵者赶回东方,直到最终在与一支阿拉伯大军的战斗中陷入绝境,她战斗到最后一刻,死时剑仍在手。